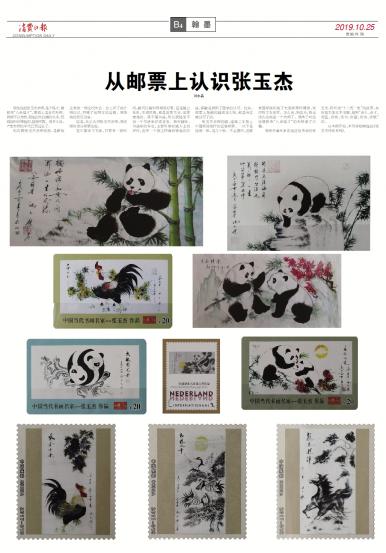B2:观察
《弄堂深处的阁楼》是一部很奇特的小说,说它奇特,并不是因为其中写了多么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恰恰相反。当你合上书,将它搁置一边的时候,会一时想不起刚才看的是些什么东西,童年的见闻?一些似是而非的叙述?好像都不是,而当你重新打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接下去读的时候,一种独特的新鲜感又再一次地抓住了你的身心。也许,这样的阅读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对真实的暗示。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作者似乎要通过孙小刚这一小说主人公,带领读者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去重新经历一遍某些人的生活,然而,所有的故事又不是既定的,事先设计好的,而是随着叙述的展开,从内部生成的。这样的一种叙事手法,我们有一个现成的名词可以套用——意识流。 说到意识流,我们马上会想起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夫等一大批十九、二十世纪著名的现代文学奠基人,但也许还要更早,这样写作手法可能会无意识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对真实有着特殊癖好的作家笔下,只是当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对其进行概括而已。在这里,我无意对意识流写作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和理论上的阐述,只想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何以当意识流写作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传统的今天,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现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在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暂辉煌后,慢慢走向了沉寂。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向了市场,迎合着大众的口味,这原也无可厚非,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本来就是少部分人的象牙之塔。可为什么在这些象牙塔里,意识流小说以及所有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却依然形单影只,郁郁而不得志呢?
问题恰恰出在象牙塔本身。在中国,象牙塔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所组成的。一部分,是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知名作家,他们已经在文学界里争得一席之地,可以轻松地获得各种写作资源,写作对他们来说,只要按照既定的路子走就行了,作品出来后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惯性,任何文体上的创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部分是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文学批评家们,照理说,这部分群体应该是对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最为敏感和最具有判断力的人,文学的发展和革新给了他们更为丰富的研究课题。但事实是,我国的现代文艺理论研究貌似丰富,其实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这就像心理学一样,研究了几个世纪,可你去心理医生那里看个病到底没有如去皮肤科看个荨麻疹来得容易。问题并不出在医生身上,而是病的不同,谁让你得的是那种复杂而又难以界定的心理毛病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相当历史感的国度,它的历史文献要比西方早几千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光是一部史书,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叙事文学,它对后世的传统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红楼梦》,所有的章回小说,甚至是戏曲,其实质都是在写史,家国的历史以及个人的历史。既然是写史,一切都必须从现实出发,讲究事件的前因后果、起承转合等一系列外在的、逻辑的联系,有铺垫、有过渡、有高潮、有收束,合乎文法,通于古今,经得起反复地推敲和把玩。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学刚刚才开始起步,马上又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上去了,传统太强大了,在传统的语境中,小说的价值标准和艺术评判立刻昭然若揭,批评家们轻车熟路,小说家们也排定了座次,这是一桩皆大欢喜的买卖,谁要是企图打破这种默契,那只能说明他学艺不精、动机不纯。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弄堂》这部小说只能算作后者,原因是它没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核心事件,人物的命运也不够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仅仅叙述了一个孩子和他父辈们的一些弄堂、学校和单位的生活经历,都是一些小事,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作者似乎志不在此,他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写得那么深刻而具体,活灵活现得仿佛就在眼前,这就使得故事超出了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某种象征,或者说隐喻。例如,孙小刚告发同学张琪吸烟的那段,表面上看,孙小刚这么做显然是想向班主任“冒号”邀功,借此获得老师的信任,但如果联系到上文他和李军通过对不受同学欢迎的张琪的戏弄,占据了绝对的心理优势,后来又因为后者用零花钱笼络同学而心怀不满来看,告发似乎还带有着一定的嫉妒和报复意味。接着,照理说,告发朋友,心里难免会对被告发者有一种愧疚之情,然而孙小刚却不,他继续保持着对张琪的优越感,继续对其进行百般地嘲弄,一切似乎都那么的不和“情理”,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实,及至后来作者写到“我就是要让他搞搞清楚,谁才是真正主宰他命运的人,他自己又是一个什么东西!找到自信的另一扇大门又奇迹般地向我敞开了,多么艰难而又轻而易举啊!”,一切才惑然开朗,联想到主人公长久以来在家和学校所受到的自我压抑,我们对于告密者的心理勘察又多了一道深刻的纬度,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现实的隐喻呢?《弄堂》这部小说就是这样,看起来,故事琐碎而不连贯,实则环环相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果说《弄堂》这部小说缺少了核心情节强烈的戏剧冲突,你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事实上,小说的冲突并不在故事上,而在于作者的主观叙述。前面说过,作者似乎是要带领读者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去重新体验当时的生活,然而,作者在这里担任的其实是一种双重身份,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和读者一样,也是一个体验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从一开始便落在了一个名叫孙小刚的孩子身上,用他的口吻和视角展开叙事,可作者毕竟是一个成人,观察事物难免会带有成人的偏好,因此,小说便一直在儿童视角和成人笔触之间来回摇摆不定,这种情况如果换作别的作者,一定会舍弃其中的一个,而选择自己最为擅长的另一个来保证叙述的统一性。可作者却偏不,他任由这两种不同的叙事性格彼此冲突着,这样的冲突在小说“原型”以及“现实和幻想”两节中到达了高潮,作者突然全盘否定了之前叙事的合理性,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使两者实现了和解,这样的叙事手法本身就极具张力。
以上是我对《弄堂》这部小说的一些个人浅见,作品更多的内涵还有待读者和评论家们进一步去梳理和发掘。真实是什么,也许目前尚无定论,但我们很欣喜地发现,在玄幻、仙侠、搞笑充斥泛滥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小说家们为了追寻他们心目当中的真实而踽踽独行,这就足够了。 (刘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