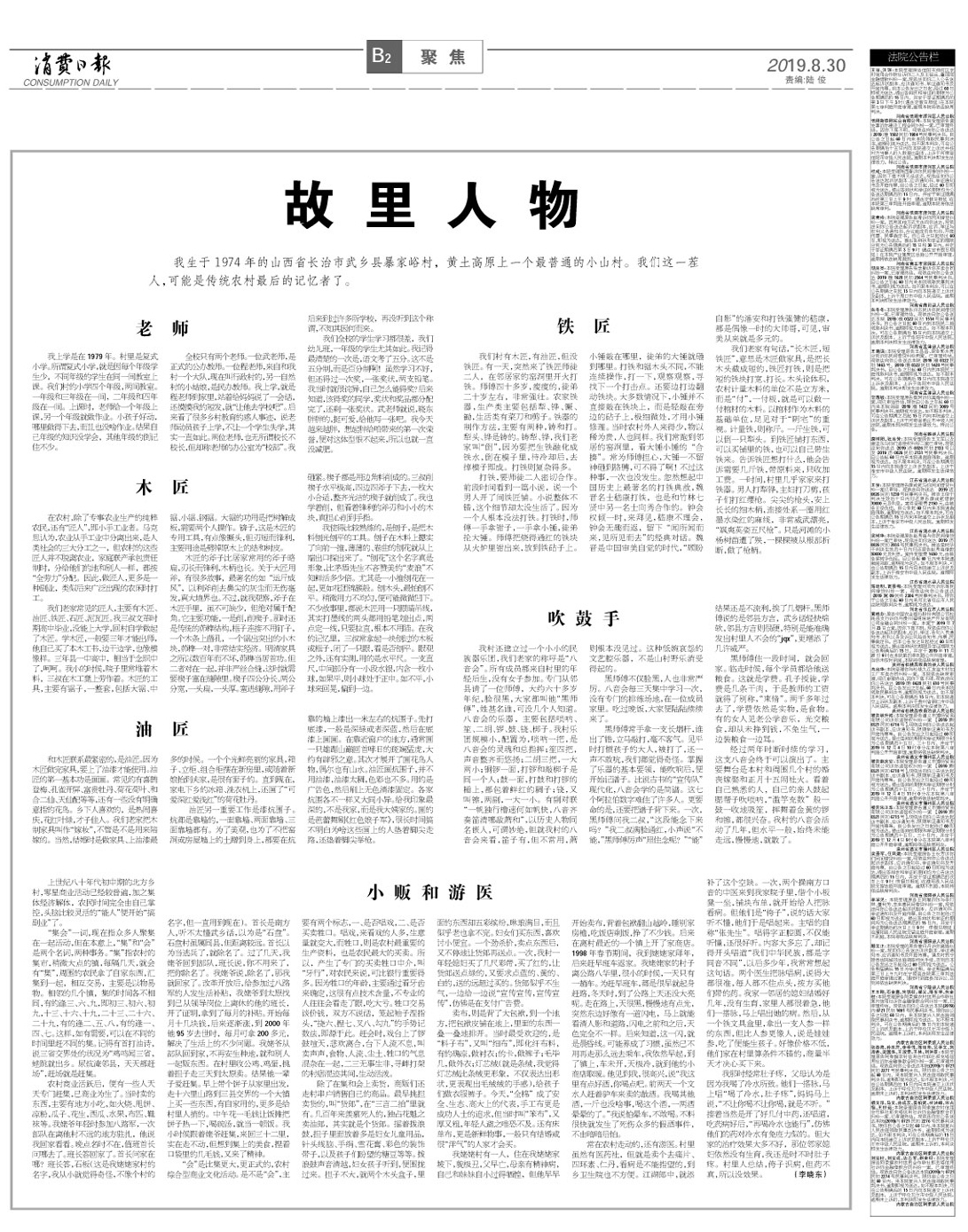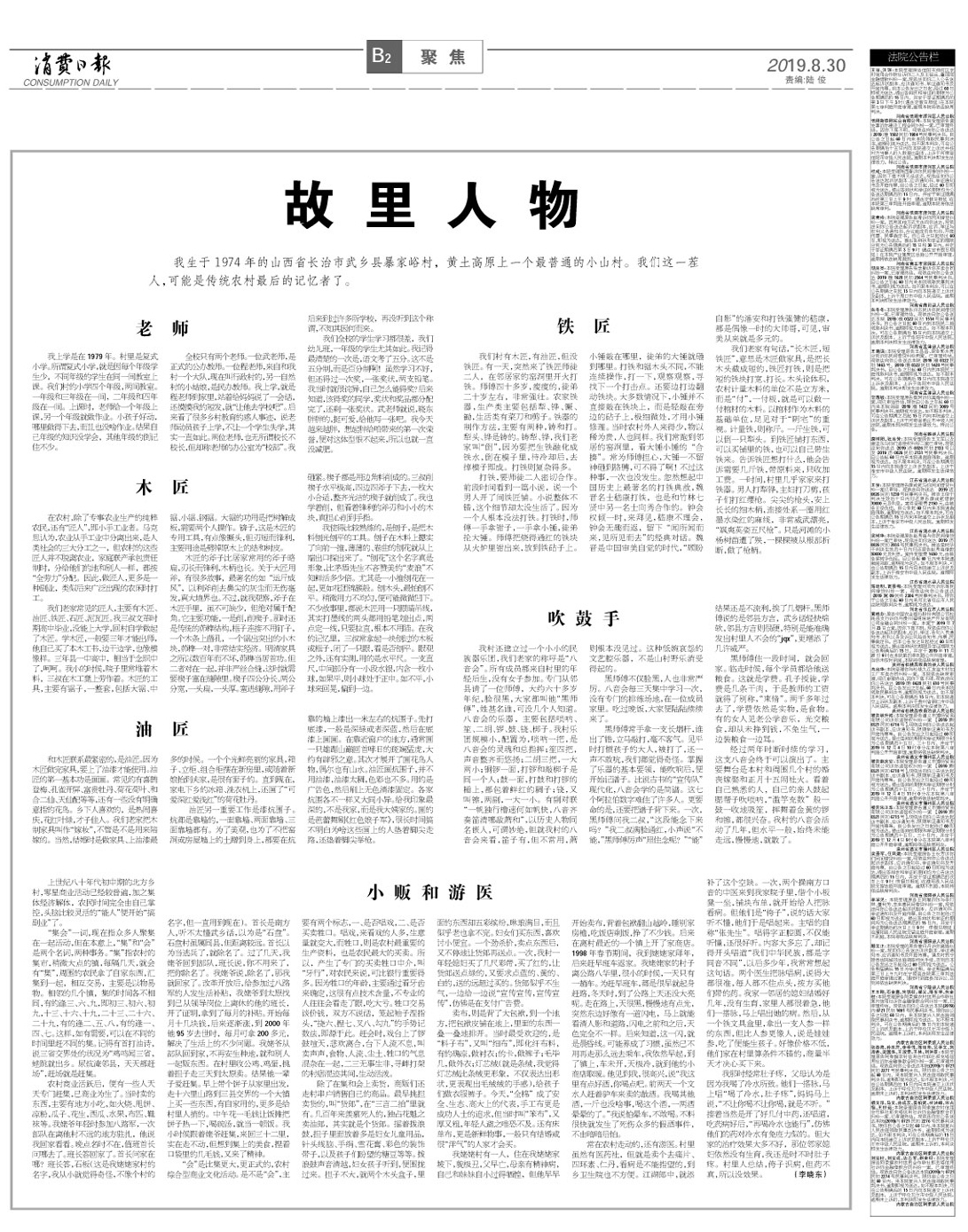
A6:视点
我生于1974年的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暴家峪村,黄土高原上一个最普通的小山村。我们这一茬人,可能是传统农村最后的记忆者了。
老师
我上学是在1979年。村里是复式小学。所谓复式小学,就是因每个年级学生少,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我们村的小学四个年级,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间,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间。上课时,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小孩子好动,哪里做得下去,而且也没啥作业。结果自己年级的知识没学会,其他年级的倒记住不少。
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武老师,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一位程老师,来自和我村一个大队,现在叫行政村的,另一自然村的小姑娘,是民办教师。我上学,就是程老师到家里,站着给妈妈说了一会话,还摸摸我的短发,就“让他去学校吧”。后来看了很多乡村教育的感人事迹,说老师动员孩子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失学,其实一直如此。两位老师,也无所谓校长不校长,但却称老师的办公室为“校部”。我后来到过许多所学校,再没听到这个称谓,不知其因何而来。
我们全校的学生学习都很差,我们幼儿班,一年级的学生尤其如此。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语文考了五分。这不是五分制,而是百分制啊!虽然学习不好,但还得过一次奖,一张奖状,两支铅笔。我当时就很诧异,自己怎么能得奖?后来知道,该得奖的同学,奖状和奖品都分配完了,还剩一张奖状。武老师就说,晓东胖胖的,挺可爱,给他写一张吧。我今天越来越胖,想起胖给咱带来的第一次荣誉,便对这体型恨不起来,所以也就一直没减肥。
木匠
在农村,除了专事农业生产的纯粹农民,还有“匠人”,即小手工业者。马克思认为,农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的三大分工之一,但农村的这些匠人并不脱离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给他们的地和别人一样,都按“全劳力”分配。因此,做匠人,更多是一种副业,类似后来广泛出现的农闲时打工。
我们老家常见的匠人,主要有木匠、油匠、铁匠、石匠、泥瓦匠。我三叔文革时期高中毕业,没能上大学,回村自学做起了木匠。学木匠,一般要三年才能出师,他自己买了本木工书,边干边学,也像模像样。三年县一中高中,相当于念职中了,呵呵。我小的时候,院子里常堆着木料,三叔在木工凳上劳作着。木匠的工具,主要有锯子,一整套,包括大锯、中锯、小锯、钢锯。大锯的功用是把树解成板,需要两个人操作。锛子,这是木匠的专用工具,有点像镢头,但刃短而锋利,主要用途是劈掉原木上的结和树皮。
木匠的斧子比居家常用的斧子略扁,刃长而锋利,木柄也长。关于大匠用斧,有很多故事,最著名的如“运斤成风”,以利斧削去鼻尖的灰尘而无伤毫发,真大境界也。不过,就我观察,斧子在木匠手里,虽不可缺少,但绝对属于配角。它主要功能,一是削,削楔子。那时还是传统的茆榫结构,框子连接不用钉子,一个木条上凿孔,一个锯出突出的小木块,茆榫一对,非常结实经济。明清家具之所以数百年而不坏,茆榫当居首功。但二者对在一起,并非严丝合缝,这时就需要楔子塞在缝隙里。楔子四公分长、两公分宽,一头扁,一头厚。塞进缝隙,用斧子砸紧。楔子都是用边角料削成的。三叔削楔子水平极高,四边四斧子下去,一枚大小合适,整齐光洁的楔子就削成了。我也学着削,但看着锋利的斧刃和小小的木块,真担心削到手指。
我使得比较熟练的,是刨子,是把木料刨光刨平的工具。刨子在木料上摁实了向前一推,薄薄的、卷曲的刨花就从上端出口探出来了。“刨花”这个名字真是形象,比茅盾先生不吝赞美的“麦浪”不知鲜活多少倍。尤其是一小推刨花在一起,更如花团锦簇般。刨木头,最怕刨不平。稍微用力不均匀,便可能微微凹下。不少故事里,都说木匠用一只眼睛吊线,其实打墨线的两头都用铅笔划出点,两点定一线,只要拉直,根本不用瞄。在我的记忆里,三叔常拿起一块刨过的木板或框子,闭了一只眼,看是否刨平。眼观之外,还有实测,用的是水平尺。一支直尺,中间部分有一小段水银,内含一枚小球,如果平,则小球处于正中。如不平,小球来回晃,偏到一边。
油匠
和木匠联系最紧密的,是油匠。因为木匠做完家具,要上了油漆才能使用。油匠的第一基本功是画画。常见的有喜鹊登梅、孔雀开屏、富贵牡丹、荷花荷叶、和合二仙、天仙配等等,还有一些没有明确意指的花鸟。乡下人喜欢的,是热闹喜庆,花红叶绿,才子佳人。我们老家把木制家具叫作“嫁妆”,不管是不是用来陪嫁的。当然,结婚时是做家具、上油漆最多的时候。一个个光鲜亮丽的家具,箱子、立柜、组合柜摆在新房里,或随着新娘抬到夫家,是很有面子的。直到现在,家电下乡的冰箱、洗衣机上,还画了“可爱深红爱浅红”的荷花牡丹。
油匠另一重要工作是漆炕围子。炕都是靠墙的,一面靠墙、两面靠墙、三面靠墙都有。为了美观,也为了不把窑洞或房屋墙上的土蹭到身上,都要在炕靠的墙上漆出一米左右的炕围子。先打底漆,一般是深绿或者深蓝,然后在底漆上画画。在靠近窗户的地方,通常画一只雄踞山巅回首哮日的斑斓猛虎,大约有辟邪之意。其次才展开了画花鸟人物,偶尔也有山水。油匠画炕围子,并不用油漆,油漆太稠,色彩也不多。用的是广告色,然后刷上无色清漆固定。各家炕围各不一样又大同小异。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家,而是我大姨家的。画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长时间搞不明白为啥这些画上的人垫着脚尖走路,还垫着脚尖举枪。
铁匠
我们村有木匠,有油匠,但没铁匠。有一天,突然来了铁匠师徒二人,在邻居家的窑洞里开火打铁。师傅四十多岁,瘦瘦的,徒弟二十岁左右,非常强壮。农家铁器,生产类主要包括犁、铧、镢、锄,生活类有菜刀和剪子。铁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两种,铸和打。犁头、铧是铸的。铸犁、铧,我们老家叫“倒”,因为要把生铁融化成铁水,倒在模子里,待冷却后,去掉模子即成。打铁则复杂得多。
打铁,要师徒二人密切合作。前段时间看到一篇小说,说一个男人开了间铁匠铺。小说整体不错,这个细节却太没生活了。因为一个人根本没法打铁。打铁时,师傅一手拿钳子,一手拿小锤,徒弟抡大锤。师傅把烧得通红的铁块从火炉里钳出来,放到铁砧子上。小锤敲在哪里,徒弟的大锤就砸到哪里。打铁和锯木头不同,不能连续操作,打一下,观察观察,寻找下一个打击点。还要边打边翻动铁块。大多数情况下,小锤并不直接敲在铁块上,而是轻敲在旁边的砧子上,极细微处,才用小锤修理。当时农村外人来得少,物以稀为贵,人也同样。我们常跑到邻居的窑洞里,看大锤小锤的“合揍”。常为师傅担心,大锤一不留神砸到胳膊,可不得了啊!不过这种事,一次也没发生。忽然想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打铁典故,魏晋名士嵇康打铁,也是和竹林七贤中另一名士向秀合作的。钟会权倾一时,来拜见,嵇康不理会,钟会无趣而返,留下“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经典对话。魏晋是中国审美自觉的时代,“顾盼自影”的潘安和打铁强健的嵇康,都是偶像一时的大帅哥,可见,审美从来就是多元的。
我们老家有句话,“长木匠,短铁匠”,意思是木匠做家具,是把长木头截成短的,铁匠打铁,则是把短的铁块打宽、打长。木头论体积,农村计量木料的单位不是立方米,而是“付”,一付板,就是可以做一付棺材的木料。以棺材作为木料的基础单位,足见对于“阴宅”的重视。计量铁,则称斤。一斤生铁,可以倒一只犁头。到铁匠铺打东西,可以买铺里的铁,也可以自己带生铁来。告诉铁匠想打什么,他会告诉需要几斤铁,带原料来,只收加工费。一时间,村里几乎家家来打铁器。男人打犁铧,主妇打刀剪,孩子们打红缨枪。尖尖的枪头,安上长长的细木柄,连接处系一圈用红墨水染红的麻线,非常威武漂亮,“飒爽英姿五尺枪”。只是河滩的小杨树苗遭了殃,一棵棵被从根部折断,做了枪柄。
吹鼓手
我村还建立过一个小小的民族器乐团,我们老家的称呼是“八音会”。所有成员都来自村里的年轻后生,没有女子参加。专门从邻县请了一位师傅,大约六十多岁年纪,脸很黑,大家都叫他“黑师傅”,姓甚名谁,可没几个人知道。八音会的乐器,主要包括唢呐、笙、二胡、锣、鼓、铙、梆子。我村乐团规模小,配置为,唢呐一把,是八音会的灵魂和总指挥;笙四把,声音整齐而悠扬;二胡三把,一大两小;铜锣一面,打锣和敲梆子是同一个人;鼓一面,打鼓和打锣的棰上,都包着鲜红的稠子;铙,又叫镲,两副,一大一小。有副对联“一帆独行橹速何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哪敌萧和”,以历史人物同名嵌入,可谓妙绝,但就我村的八音会来看,笛子有,但不常用,萧则根本没见过。这种低婉哀怨的文艺腔乐器,不是山村野乐消受得起的。
黑师傅不仅脸黑,人也非常严厉。八音会每三天集中学习一次,没有专门的排练场地,在一位成员家里。吃过晚饭,大家便陆陆续续来了。
黑师傅常手拿一支长烟杆,谁出了错,立马敲打,毫不客气。见平时打惯孩子的大人,被打了,还一声不敢吭,我们都觉得奇怪。掌握了乐器的基本要领,能吹响后,便开始记谱子。比说古书的“宣传队”现代化,八音会学的是简谱。这七个阿拉伯数字难住了许多人。更要命的是,还要把谱子背下来。一次,黑师傅问我二叔,“这段能念下来吗?”我二叔满脸通红,小声说“不能,”黑师傅厉声“照住念呢?”“能”结果还是不流利,挨了几烟杆。黑师傅说的是邻县方言,武乡话轻快绵软,邻县方言则很硬,特别是能准确发出村里人不会的“jqx”,更增添了几许威严。
黑师傅住一段时间,就会回家。临走时候,每个学员都给他送粮食。这就是学费。孔子授徒,学费是几条干肉,于是教师的工资就得了别称,“束脩”。两千多年过去了,学费依然是实物,是食物。有的女人见老公学音乐,光交粮食,却从未挣到钱,不免生气,一边装粮食一边骂。
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学习,这支八音会终于可以演出了。主要舞台是本村和周围几个村的婚丧嫁娶和正月十五闹社火。看着自己熟悉的人,自己的亲人鼓起腮帮子吹唢呐,“滥竽充数”般一鼓一收地吸笙,挥舞着金黄的锣和镲,都很兴奋。我村的八音会活动了几年,但水平一般,始终未能走远,慢慢地,就散了。
小贩和游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北方乡村,零星商业活动已经较普遍,加之集体经济解体,农民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控,头脑比较灵活的“能人”便开始“搞副业”了。“集会”一词,现在指众多人聚集在一起活动,但在本意上,“集”和“会”是两个名词,两种事务。“集”指农村的集市,稍微大点的镇,每隔几天,就会有“集”,周围的农民拿了自家东西,汇集到一起,相互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相邻的几个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有的逢三、六、九,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有的逢二、五、八,有的逢一、四、七。这样,如有需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赶不同的集。记得有首打油诗,说三省交界处的状况为“鸡鸣闻三省,蛙跳就出乡。尿炕淹邻县,天天都赶场”,赶场就是赶集。
农村商业活跃后,便有一些人天天专门赶集,已商业为生了。当时卖的东西,主要有地方小吃,如火烧、甩饼、凉粉,瓜子、花生,西瓜、水果,布匹、鞋袜等。我姥爷年轻时参加八路军,一次部队在离他村不远的地方驻扎,他说我回家看看。晚点名时不在,值班首长问哪去了。班长答回家了。首长问家在哪?班长答,石板(这是我姥姥家村的名字,我从小就觉得奇怪,不像个村的名字,但一直用到现在)。首长是南方人,听不太懂武乡话,以为是“石盘”。石盘村虽属同县,但距离较远。首长以为当逃兵了,就除名了。过了几天,我姥爷回到部队,班长说,你不用来了,把你除名了。我姥爷说,除名了,那我就回家了。改革开放后,给参加过八路军的人发生活补贴,我姥爷到太原找到已从领导岗位上离休的他的班长,开了证明,拿到了每月的补贴。开始每月十几块钱,后来逐渐涨,到2000年他95岁去世时,每月可拿200多元,解决了生活上的不少问题。我姥爷从部队回到家,不再安生种地,就和别人一起贩东西。在村里收公鸡、鸡蛋,挑着担子走三天到太原卖。结果他一辈子爱赶集。早上带个饼子从家里出发,走十六里山路到三县交界的一个大镇上买一些东西,有自家用的,更多是给村里人捎的。中午花一毛钱让饭摊把饼子热一下,喝碗汤,就当一顿饭。我小时候跟着姥爷赶集,来回三十二里,实在走不动,但想到集上的美食,捏着口袋里的几毛钱,又来了精神。“会”是比集更大,更正式的,农村综合型商业文化活动。是不是“会”,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否唱戏,二、是否买卖牲口。唱戏,来看戏的人多,生意量就变大,而牲口,则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大的买卖。所以,产生了专门的买卖牲口中介,叫“牙行”,对农民来说,可比银行重要得多。因为牲口的年龄,主要通过看牙齿来确定,这很有点技术含量,不专业的人往往会看走了眼,吃大亏。牲口交易谈价钱,双方不说话,笼起袖子涅指头,“挠六、捏七、叉八、勾九”的手势记数法,即源于此。赶会时,戏台上了锣鼓喧天,悲欢离合,台下人流不息,叫卖声声,食物、人流、尘土、牲口的气息混杂在一起,二三无事生非,寻衅打架的村痞混迹其间,生动活泼。
除了在集和会上卖货,商贩们还走村串户销售自己的商品。最早挑担卖货的,叫“货郎”,在“三言二拍”里就有。几百年来羡慕死人的,独占花魁之卖油郎,其实就是个货郎。摇着拨浪鼓,担子里面放着多是妇女儿童用品,针头线脑、手绢、雪花膏、彩色的装饰带子,以及孩子们盼望的糖豆等等。拨浪鼓声音清越,妇女孩子听到,便围拢过来。担子不大,就两个木头盒子,里面的东西却五彩缤纷,琳琅满目,而且似乎老也拿不完。妇女们买东西,喜欢讨小便宜。一个劲杀价,卖点东西后,又不停地让货郎再送点。一次,我村一年轻媳妇买了几尺彩带,买了红的,让货郎送点绿的,又要求点蓝的、黄的、白的,送的远超过买的。货郎似乎不生气,一边给一边说“宣传宣传,宣传宣传”,仿佛是在支付广告费。
卖布,则是背了大包袱,到一个地方,把包袱皮铺在地上,里面的东西一叠一叠地排开。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料子布”,又叫“细布”,即化纤布料,有的确凉,做衬衣;的卡,做裤子;毛毕几,做外衣;灯芯绒(就是条绒,我觉得灯芯绒比条绒更形象,不仅表达出形状,更表现出毛绒绒的手感),给孩子们做衣服裤子。今天,“全棉”成了安全、生态、高大上的代表,手工布更是成功人士的追求,但当时叫“笨布”,又厚又粗,年轻人避之唯恐不及。还有床单布,更是新鲜物事,一般只有结婚或很“洋气”的人家才会买。
我姥姥村有一人,住在我姥姥家坡下,貌极丑,父早亡,母亲有精神病,自己和妹妹自小过得牺惶,但他早早开始卖布,背着包袱翻山越岭,睡别家房檐,吃饭店剩饭,挣了不少钱。后来在离村最近的一个镇上开了家商店。1998年春节期间,我到姥姥家拜年,后来赶早班车返家。我姥姥家的村子离公路八华里,很小的时候,一天只有一趟车。为赶早班车,都是很早就起身赶路,冬天时,到了公路上天还没大亮呢。走在路上,天很黑,慢慢地有点光,突然东边好像有一道闪电,马上就能看清人影和道路,闪电之前和之后,天色完全不一样。后来知道,这一闪,就是晨昏线。可能养成了习惯,虽然已不用再走那么远去乘车,我依然早起,到了镇上,车未开,天极冷,就到他的小商店取暖。他见到我,很高兴,说“我这里有点好酒,你喝点吧。前两天一个文水人赶着驴车来卖的散酒。我喝其他酒,一斤也没啥事,喝这个酒,一两酒晕晕的了。”我说怕晕车,不敢喝。不料很快就发生了死伤众多的假酒事件,不由暗暗后怕。
常在农村走动的,还有游医。村里虽然有医药社,但就是卖个去痛片、四环素、仁丹,看病是不能指望的,到乡卫生院也不方便。江湖郎中,就添补了这个空缺。一次,两个操南方口音的中医来到我家院子里,借个小板凳一坐,铺块布单,就开始给人把脉看病。但他们是“侉子”,说的话大家听不懂,他们于是唱起来。主唱的自称“张先生”。唱得字正腔圆,不仅能听懂,还很好听。内容大多忘了,却记得开头唱道“我们中华民族,都是字同音不同”,以后多少年,我常常想起这句话。两个医生把脉唱病,说得大都很准,每人都不住点头,按方买他们带的药。我家一邻居的媳妇结婚好几年,没有生育,家里人都很着急,他们一搭脉,马上唱出她的病。然后,从一个铁文具盒里,拿出一支人参一样的东西,但比人参更像人,说是娃娃参,吃了便能生孩子。好像价格不低,他们家在村里算条件不错的,商量半天才决心买下来。
我那时经常肚子疼,父母认为是因为我喝了冷水所致。他们一搭脉,马上唱“喝了冷水,肚子疼”,妈妈马上说,“不让你喝不让你喝,就是不听。”接着当然是开了好几付中药,还唱道,吃药病好后,“再喝冷水也能行”,仿佛他们的药对冷水有免疫力似的。但大家的治疗效果大多不好,那位邻家媳妇依然没有生育,我还是时不时肚子疼。村里人总结,侉子识病,但药不真,所以没效果。 (李晓东)
(消费日报 www.xfrb.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