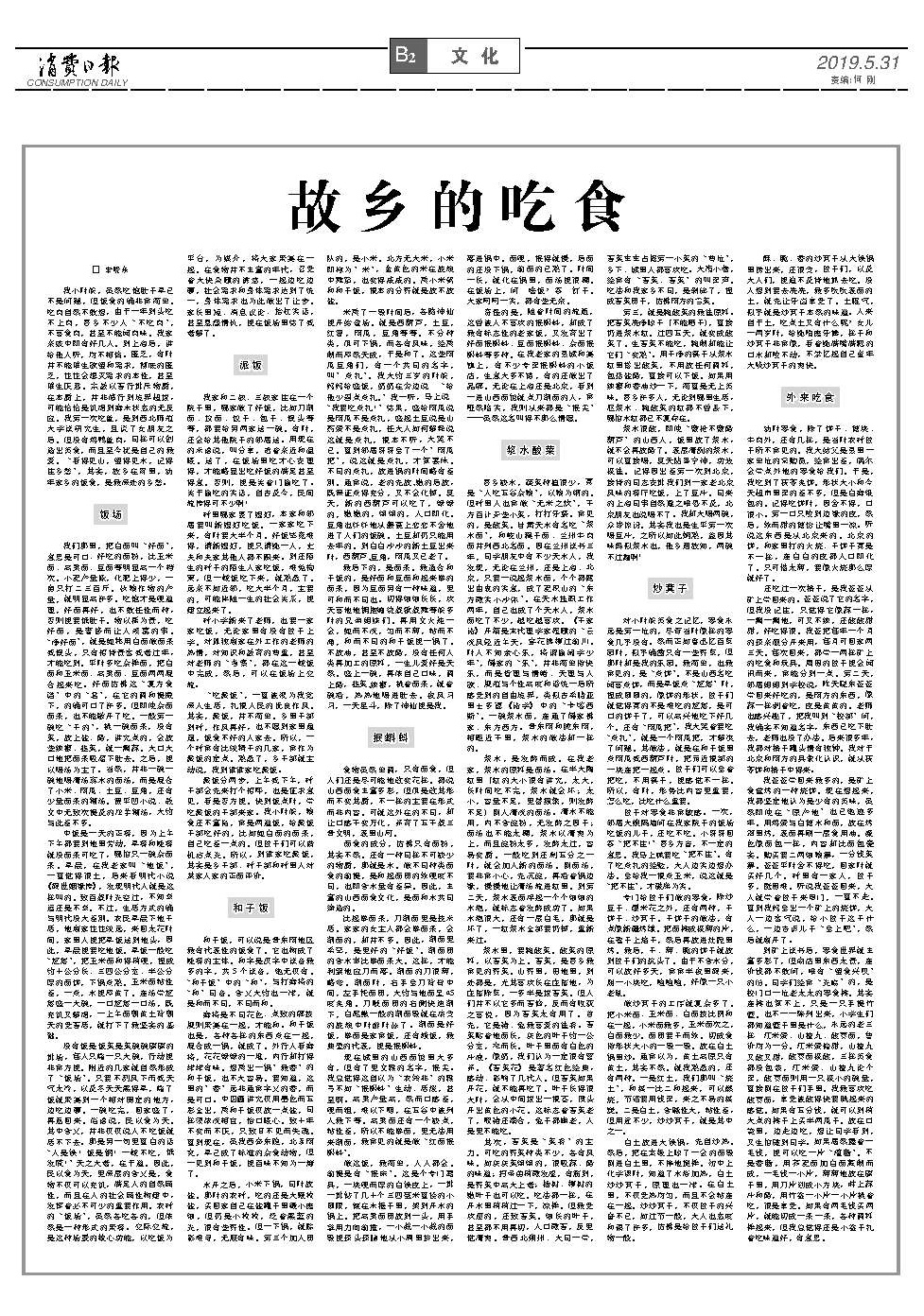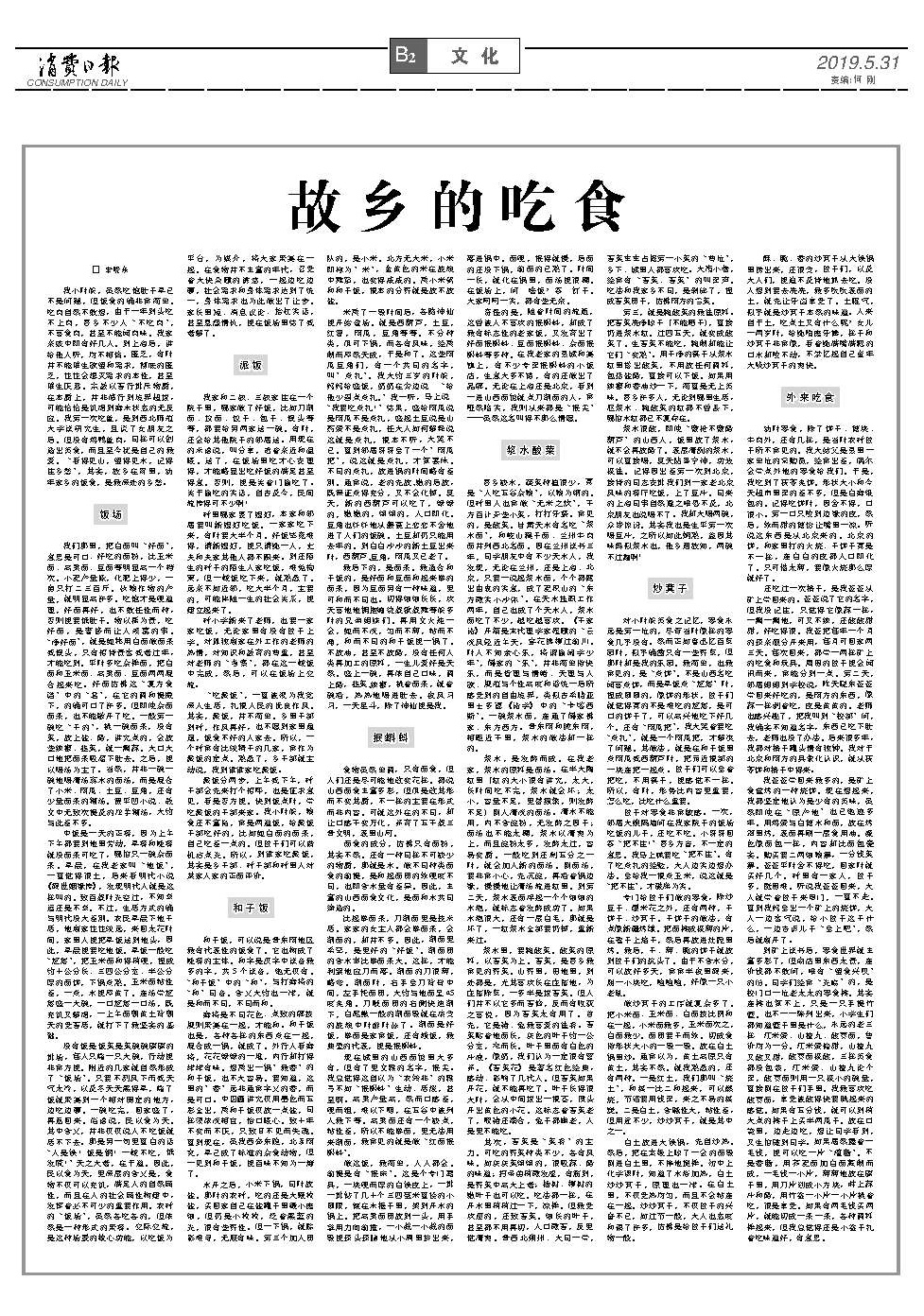
A6:文化
□ 李晓东
我小时候,虽然吃饱肚子早已不是问题,但饭食的确非常简单。吃肉自然不敢想,由于一年到头吃不上肉,吾乡不少人“不吃肉”,不喜食肉,甚至不能闻肉味。我家亲戚中即有好几人。到上海后,讲给他人听,均不相信。匮乏,有时并不能催生欲望和需求,彻底的匮乏,往往会熄灭需求的本性,甚至催生厌恶。宗教以苦行排斥物质,在本质上,并非修行到境界超拔,可能恰恰是饥渴到麻木状态的无反应。我第一次吃鱼,是到西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且谈了女朋友之后。但没有鸡鸭鱼肉,同样可以创造出美食,而且至今犹是自己的最爱。“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其实,故乡在胃里,幼年家乡的饭食,是最深处的乡愁。
饭场
我们那里,把白面叫“好面”,意思是可口、好吃的面粉,比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明显高一个档次。小麦产量低,化肥上得少,一亩只打二三百斤。秋粮作物的产量,就明显高许多。吃饱才是硬道理,好面再好,也不敢任性而种,否则便要饿肚子。物以稀为贵,吃好面,是奢侈而让人羡慕的事。“净好面”,就是纯粹用白面做面条或馒头,只有招待贵客或者过年,才能吃到。平时多吃杂拌面,把白面和玉米面、高粱面、豆面两两混合起来吃。好面仿佛这“复方食谱”中的“君”,在它的调和提振下,的确可口了许多。但即使杂面面条,也不能敞开了吃。一般第一碗吃“干的”,挑一碗面条,没有菜,放上盐、醋,讲究点的,会放些辣椒、韭菜,就一瓣蒜。大口大口地把面条吸溜下肚去。之后,便以喝汤为主了。当然,并非一碗一碗地喝清汤寡水的面汤,而是混合了小米、南瓜、土豆、豆角,还有少量面条的糊汤。贾平凹小说、散文中无数次提及的洋芋糊汤,大约与此差不多。
中饭是一天的正餐,因为上午下午都要到地里劳动,早餐和晚餐就没面条可吃了,哪怕只一碗杂面条。早晨,在我老家叫“地饭”,一直觉得很土,后来看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发现明代人就是这样叫的。数百载时光空过,不知幸运还是不幸。不过,生活方式的确与明代没大差别。农民早晨下地干活,地离家往往较远,来回太花时间,家里人便把早饭送到地头,因此,早晨便要吃地饭。早饭一般吃“疙瘩”,把玉米面和得稍硬,捏成约十公分长、三四公分宽、半公分厚的面饼,下锅煮熟。玉米面粘性差,一煮,水便浑黄了。连汤带疙瘩盛一大碗,一口疙瘩一口汤,既充饥又解渴,一上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活,就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没有饭是饭菜是菜碗碗碟碟的排场,每人只端一只大碗,行动便非常方便。附近的几家就自然形成了“饭场”。只要不刮风下雨或天气太冷,以及冬天天黑得早,端了饭就聚集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边吃边聊。一碗吃完,回家盛了,再返回来。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其中含义,并非仅仅说人不吃饭就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句更直白的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发慌!”天之大者,在于道。因此,民以食为天,更深层的含义是,食物不仅可以充饥,满足人的自然属性,而且在人的社会属性构建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农村的“饭场”,虽然各吃各的,但依然是一种形式的聚餐。交际交流,是这种场景的核心功能,以吃饭为平台,为媒介,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在食物并不丰富的年代,忍受着大快朵颐的诱惑,一起边吃边聊,社会需求和身体需求达到了统一,身体需求也为此做出了让步。家长里短、消息议论、抬杠笑话,甚至恩怨情仇,便在饭场里结了或者解了。
派饭
我家和二叔、三叔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哪家做了好饭,比如刀削面、拉面、饺子、包子、馒头等等,都要给另两家送一碗。有时,还会给其他院子的邻居送。用现在的术语说,叫分享,透着亲近和温暖。送了,在饭场里吃才心安理得,才能略显出吃好饭的满足甚至得意。否则,便是关着门偷吃了。关于偷吃的笑话,自古及今,民间流传得可不少啊!
村里哪家娶了媳妇,本家和邻居要叫新媳妇吃饭。一家家吃下来,有时要大半个月。好饭毕竟难得,请新媳妇,便只请她一人,丈夫和夫家其他人都不跟来。到还陌生的村子的陌生人家吃饭,难免拘束,但一顿饭吃下来,就熟悉了。远亲不如近邻,吃大半个月,主要的,可能伴随一生的社会关系,便建立起来了。
村小学新来了老师,也要一家家吃饭,无论家里有没有孩子上学。对孤独离家在外工作的老师的热情,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甚至对老师的“考察”,都在这一顿饭中完成,然后,可以在饭场上交流。
“吃派饭”,一直被视为我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优良作风。其实,派饭,并不简单。乡里干部到村,作风再好,也不愿到家里邋遢,饭食不好的人家去。所以,一个村常有比较精干的几家,常作为派饭的定点。熟悉了,乡干部就主动说,我到谁谁家吃派饭。
派饭分两步,上午或下午,村干部会先来打个招呼,也是征求意见,看是否方便。快到饭点时,带吃派饭的干部来家。我小时候,粮食还不富裕,常是两道饭,给派饭干部吃好的,比如纯白面的面条,自己吃差一点的。但孩子们可以借机沾点光。所以,到谁家吃派饭,其实是乡干部、村干部和村里人对某家人家的正面评价。
和子饭
和子饭,可以说是晋东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饭食了。它也构成了晚餐的主体。和字是汉字中读音最多的字,共5个读音,绝无仅有。“和子饭”中的“和”,与打麻将的“和”同音。含义大约也一律,就是和而不同,不同而和。
麻将是不同花色、点数的牌按规则聚集在一起,才能和。和子饭也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煮在一起,混合成一锅,就成了。外行人看麻将,花花绿绿的一堆,内行却打得津津有味。想熬出一锅”最香”的和子饭,也不大容易。要知道,这里的”香”远非通常字义的香,而是可口。中国画讲究仅用墨色而五彩全出,熬和子饭仅放一点盐,同样须浓淡相宜,怡口暖心。数十年不变而不厌,只数日不见而失魂。直到现在,虽我西奔东跑,北豕南突,早己成了标准的杂食动物,但一见到和子饭,便百味不知为一痴了。
水开之后,小米下锅,同时放盐。那时的农村,吃的还是大颗粒盐,买回家自己在盐罐子里碾小磨细,但仍是小粒粒,泛着黑蓝的光,很有些野性。但一下锅,就踪影难寻,无痕有味。第三个加入团队的,是小米。北方无大米,小米即称为”米”,金黄色的米在波浪中舞蹈,也变得咸咸的。熬小米粥和和子饭,根本的分野就是放不放盐。
米熬了一段时间后,各路神仙便开始登场。就是西葫芦,土豆,红薯,南瓜,豆角等等。不分种类,俱可下锅,而各有风味,经熬制而浑然天成,于是和了。这些南瓜豆角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煮扎”。我大约三岁的时候,妈妈给盛饭,奶奶在旁边说:“给他少舀点煮扎。”我一听,马上说:“我要吃煮扎!”结果,盛给南瓜说是南瓜不是煮扎,盛起土豆说是山药蛋不是煮扎,任大人如何解释说这就是煮扎,根本不听,大哭不已。直到邻居哥哥拿了一个”南瓜把”,说这就是煮扎,才算罢休。不同的煮扎,放进锅的时间略有差别。通常说,老的先放,嫩的后放,既保证煮得充分,又不会化掉。夏天,新的西葫芦可以吃了,绿绿的,嫩嫩的,绵绵的,入口即化。豆角也纤纤地从藤蔓上恋恋不舍地进了人们的饭碗。土豆却仍只能用去年的。到白白沙沙的新土豆出来时,西葫芦,豆角,南瓜又已老了。
最后下的,是面条。最适合和子饭的,是好面和豆面和起来擀的面条,因为豆面另有一种味道,更可和而不同也。切得细细长长,欢天喜地地拥抱缠绕载歌载舞等候多时的兄弟姐妹们。再用文火炖一会,纯而不淡,匀而不薄,粘而不滞,和而不同的和子饭便一锅了。不放油,甚至不放醋,没有任何人类再加工的原料,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盛上一碗,再依自己口味,调上醋,韭菜,辣椒,挑着面条,就着碗沿,热热地喝进肚去。夜风习习,一天星斗,除了神仙便是我。
抿蝌蚪
食物虽然单调,只有面食,但人们还是尽可能地改变花样。都说山西面食丰富多彩,但俱是改其形而不变其质,不一样的主要在形式而非内容。可就这外在的不同,却让口感千变万化,养育了五千载三晋文明,表里山河。
面食的成分,仿佛只有面粉,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同样不可缺少的物质,那就是水。做不同种类面食的前提,是和起面团的软硬度不同,也即含水量有差异。因此,丰富的山西面食文化,是面和水共同缔造的。
比起擀面条,刀削面更是技术活。家家的女主人都会擀面条,会削面的,却并不多。因此,削面更希罕,是更好的“好饭”。削面团的含水率比擀面条大。这样,才能利索地应刀而落。削面的刀很薄,略弯。削面时,右手拿刀背脊中间,左手托面团,大约与地面呈45度夹角。刀顺面团的右侧快速削下,白泥鳅一般的削面段就在滚烫的波浪中时游时泳了。削面是好饭,擀面是家常饭,还有赖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抿蝌蚪。
现在城里的山西面馆里大多有,但有了更文雅的名字,抿尖。我总觉得这自以为“农转非”的雅号不如“抿蝌蚪”生动、活泼,甚至萌。高粱产量高,然而口感差,硬而粗,难以下咽,在五谷中被列入最下等。高粱面还有一个缺点,粘性差,所以不能擀面,更无法用来削面,最常见的就是做“红面抿蝌蚪”。
做这饭,最简单,人人都会。前提是有“抿床”。这是个专门器具,一块硬而厚的白铁皮上,一排一排钻了几十个三四毫米直径的小圆眼,镶在木框子里,架到开水的锅上。把高粱面团放到一头,用手掌用力向前推,一小截一小截的面段便探头探脑地从小洞里挤出来,落进锅中。面硬,抿得就慢,后面的还没下锅,前面的已熟了。时间一长,就化在锅里,面汤便很稠。在饭场上,问:啥饭?答:钉子。大家呵呵一笑,都有些无奈。
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曾被人不喜欢的抿蝌蚪,却成了最有标志性的老家饭,又发育出了好面抿蝌蚪、豆面抿蝌蚪、杂面抿蝌蚪等多种。在我老家的县城和集镇上,有不少专卖抿蝌蚪的小饭店,生意大多不错,有的还做出了品牌。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看到一进山西面馆就点刀削面的人,常哑然暗笑,我则从来都是“抿尖”——虽然这名叫得不那么情愿。 浆水酸菜
吾乡缺水,蔬菜种植很少,真是“人吃五谷杂粮”,以粮为纲的。但村里人也常做“无米之炊”,千方百计弄些小菜,打打牙祭。常见的,是酸菜。甘肃天水有名吃“浆水面”,和岐山臊子面、兰州牛肉面并列西北名面。因在兰州读书三年,同学朋友中有不少天水人,我发现,无论在兰州,还是上海、北京,只要一说起浆水面,个个都露出由衷的笑意,成了麦积山的“东方微笑小沙弥”。在天水挂职工作两年,自己也成了个天水人,浆水面吃了不少,越吃越喜欢。《千家诗》开篇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的“云淡风轻近午天,穿花拂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儒家的“乐”,并非简单指快乐,而是哲理与情绪、天理与人欲、规范与个性高度和谐统一后所感受到的自由境界,类似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卡塔西斯”。一碗浆水面,连通了儒家佛家、东方西方。晋东南和陇东南,相距近千里,浆水的做法却一样的。
浆水,是发酵而成。在我老家,浆水的原料是面汤。在半大陶缸里(缸的大小很有讲究,太大,长时间吃不完,浆水就会坏;太小,容量不足,更替频繁,则发酵不足)倒入清淡的面汤。清水不能用,内不含淀粉,无发酵之因子;面汤也不能太稠,浆水以清爽为上,而且淀粉太多,发酵太过,容易变质。一般吃到还剩五分之一时,就会加入新的面汤。倒面汤,要非常小心,先沉淀,再沿着锅边缘,慢慢地让清汤流进缸里。到第二天,浆水表面浮起一个个细细的水泡,就标志着发酵成功了。如果水泡很大,还有一层白毛,那就是坏了,一缸浆水全部要扔掉,重新来过。
浆水里,要腌酸菜。酸菜的原料,以苦菜为上。苦菜,是吾乡最常见的野菜。山野里,田地里,到处都是,尤其喜欢长在庄稼地,为庄稼除草,一多半是拔苦菜。但人们并不以它多而苦恼,反而有收获之喜悦,因为苦菜太有用了。首先,它是猪、兔最喜爱的佳肴。苦菜贴着地面长,灰色的叶子约一公分宽,窄而长。叶子里面有白色的汁液,像奶,我们认为一定很有营养。《苦菜花》是著名红色经典,感动、影响了几代人。但苦菜如果开花,就不能再吃了。叶子长得很大时,会从中间拔出一根茎,顶头开出黄色的小花。这标志着苦菜老了,喂猪还凑合,兔子都嫌老,人是更不能吃。
其次,苦菜是“菜肴”的主力。可吃的野菜种类不少,各有风味。如灰灰菜绵绵的,很吸蒜、醋的味道;扫帚苗稍微发涩,有筋到,是野菜中高大上者;杨树、柳树的嫩叶子也可以吃。吃法都一样,在开水里稍稍过一下,凉拌。但最受欢迎的,还数苦菜。细长的叶子,甚至都不用再切,入口微苦,反更觉清爽。晋西北朔州、大同一带,苦菜牢牢占据第一小菜的“尊位”,乡下、城里人都喜欢吃。大街小巷,经常有“苦菜、苦菜”的叫卖声。吃法和我家乡不同,是剁碎了,捏成苦菜团子,仿佛南方的雪菜。
第三,就是腌酸菜的最佳原料。把苦菜洗净晾干(不能晒干),直接扔进浆水缸。过四五天,就变成酸菜了。生苦菜不能吃,腌制却能让它们“变熟”。用干净的筷子从浆水缸里搭出酸菜,不用放任何调料,包括盐醋,直接可以下饭。如果用辣椒和香油炒一下,简直是无上美味。吾乡许多人,无论到哪里生活,沤浆水、腌酸菜的缸都不曾丢下,哪怕水缸都已不复存在。
浆水很酸,即使“缴枪不缴醋葫芦”的山西人,饭里放了浆水,就不会再放醋了。表层清洌的浆水,可以直接喝,夏天防暑宁神,功效极佳。记得因出差第一次到北京,接待的同志安排我们到一家老北京风味的餐厅吃饭,上了豆汁。同来的上海同事自然避之唯恐不及,北京朋友也说喝不了。我却大喝两碗,众皆惊讶。其实我也是生平第一次喝豆汁,之所以如此娴熟,盖因其味酷似浆水也,他乡遇故知,两碗不过瘾啊!
炒萁子
对小时候美食之记忆,零食永远是第一位的,尽管当时像样的零食几乎没有。然而正如鲁迅忆百草园时,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是“煮饼”。不是山西名吃闻喜煮饼,而是早饭煮“疙瘩”时,捏成圆圆的,像饼的形状,孩子们就觉得真的不是难吃的疙瘩,是可口的饼子了,可以高兴地吃下好几个。还有“南瓜把”,我大哭着要吃“煮扎”,就是一个南瓜把,才解决了问题。其做法,就是在和子饭里煮南瓜或西葫芦时,把靠近根部的一块连把一起煮。孩子们可以拿着把吃,不用筷子,便感觉不一样。所以,有时,形势比内容更重要,怎么吃,比吃什么重要。
孩子对零食非常敏感。一次,邻居大娘隔墙问在我家院子的饭场吃饭的儿子,还吃不吃。小哥哥回答“把不住!”吾乡方言,不一定的意思。我马上喊要吃“把不住”。有了吃煮扎的经验,大人边笑边想办法。拿给我一根煮玉米,说这就是“把不住”,才破涕为笑。
专门给孩子们做的零食,除炒豆子、爆米花之外,还有两种,干饼子、炒萁子。干饼子的做法,有点像新疆烤馕。把面摊成极薄的片,在鏊子上焙干,然后再放进灶膛里烤。最后,干、薄、脆的饼子就放到孩子们的炕头了。由于不含水分,可以放好多天,常常半夜里醒来,掰一小块吃,喳喳喳,好像一只小老鼠。
做炒萁子的工序就复杂多了。把小米面、玉米面、白面按比例和在一起,小米面最多,玉米面次之,白面最少。面团要干而软。切成食指形状大小的一段一段。放在白土锅里炒。通常以为,黄土高原只有黄土,其实不然。就我熟悉的,还有两种。一是红土,我们那叫“烧土”,和煤一比二和起来,可以燃烧,节省要用钱卖,来之不易的煤炭。二是白土,含碱性大,粘性差,但用途不少,炒炒萁子,就是其中之一。
白土放进大铁锅,先自炒热。然后,把在案板上晾了一会的面段倒进白土里,不停地搅拌。初中上化学课时,知道了水浴加热,白土炒炒萁子,原理也一律。在白土里,不仅受热均匀,而且不会粘连在一起。炒炒萁子,不仅孩子的兴奋不已,如过节一般,大人也态度和蔼了许多,仿佛是给孩子们送礼物一般。
酥、脆、香的炒萁子从大铁锅里捞出来,还很烫,孩子们,以及大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抓去吃。没人想到要去洗洗,最多吹吹表面的土,就先让牙齿享受了。土腥气,似乎就是炒萁子本然的味道。人来自于土,吃点土又有什么呢?女儿一两岁时,给她啃磨牙棒,样子和炒萁子非常像,看着她满嘴满腮的口水却咬不动,不禁忆起自己童年大啖炒萁子的爽快。
外来吃食
幼时零食,除了饼干、糖块、牛肉外,还有几样,是当时农村孩子所不常见的。我大姑父是县里一家单位的采购员,经常出差,偶尔会带点外地的零食给我们。于是,我吃到了茯苓夹饼。形状大小和今天超市里卖的差不多,但是白麻纸包的。记得吃饼时,因舍不得,口很小。第一口只咬到边缘的皮,然后,软而甜的糖饴让嘴里一凉。听说这东西是从北京来的。北京的饼,和家里打的火烧、干饼子真是不一样,连白白的皮都入口即化了。只可惜太薄,要像火烧那么厚就好了。
还吃过一次橘子,是我爸爸从矿上带回来的。爸爸说了它的名字,但我没记住,只觉得它像蒜一样,一瓣一瓣地,可又不辣,还酸酸甜甜,好吃得很。我爸把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分开来用,每月可回家两三天。每次回来,都带一两样矿上的吃食和玩具。周围的孩子便会闻讯而来,常能分到一点。第二天,邻居姐姐到学校说,昨天晓东爸爸带回来好吃的,是南方的东西,像蒜一样剥着吃,皮是黄黄的。老师也感兴趣了,把我叫到“校部”问,我确实不知道名字,东西已吃下肚去,老师也没了办法。后来很多年,我都对橘子罐头情有独钟。我对于北京和南方的具象化认识,就从茯苓饼和橘子中得来。
我爸爸带回来最多的,是矿上食堂烤的一种烧饼。现在想起来,我都坚定地认为是少有的美味,虽然即使在“原产地”也已绝迹多年。用鸡蛋与白糖水和面,放在烤箱里烤,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颜色像面包一样,内容却比面包瓷实。购买要二两细粮票,一分钱菜票。爸爸平时舍不得吃,回家时就买好几个。村里有一家人,孩子多,挺困难。听说我爸爸回来,大人就带着孩子来串门,一直不走。直到我妈拿出一个矿上的烧饼,大人一边客气说,给小孩子这干什么,一边告诉儿子“拿上吧”,然后就离开了。
到矿上读书后,零食世界就丰富多彩了,但商店里东西太贵,连价钱都不敢问,唯有“望食兴叹”的份。同学们经常“光临”的,是校门口一位老太太的零食摊。其实连摊也算不上,只是一只手提竹篮。也不一一陈列出来,小学生们都知道篮子里是什么,永远的老三样:江米蛋、山楂丸、酸枣面,售价均为一分。江米蛋偏甜,山楂丸又酸又甜,酸枣面极酸,三样美食都没包装,江米蛋、山楂丸论个卖,酸枣面则用一只极小的碗量,直接倒在孩子们手里。我最喜欢吃酸枣面,享受被酸得快要跳起来的感觉。如果有五分钱,就可以到稍大点的摊子上买半两瓜子。放在口袋里,边走边吃,想让同学看到,又生怕碰到同学。如果居然握着一毛钱,便可以吃一片“灌肠”。不是香肠,用荞麦面加白面蒸制而成,一毛钱一小片,薄薄地放在碟子里,用刀片划成小方块,淋上蒜汁和醋,用竹签一小片一小片挑着吃,很是享受。如果有两毛钱买两片,就能切成一条一条,各种调料拌起来,但我总觉得还是小签子扎着吃味道好,有意思。
(消费日报 www.xfrb.com.cn)